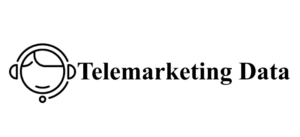在法律层面,法官是独立的。法律将未成年人视为具有权利的人 提出四个问题 。但听证会期间法官对待未成年人的目光和方式属于个人问题。简而言之,法官就是法官:他有他的实践、他的职责。他接受过律师培训并就读于国家司法学校。然后,法官们在办公室接受培训——这些都是会议,一种实践。
《刑法》中有辨别的概念:孩子能够理解我对他说的话吗?这取决于法官的决定。非常古老的 Jean Laboube 裁决将这种辨别的年龄定为七年。
在教育援助方面,情况则有所不同。在我担任青少年法官的实践中,我身边有专业人士。我曾经必须向一个十二个月大的婴儿解释如何安置婴儿。我跟他谈过了。我不知道他从我所说的内容中理解了什么,但与我共事的专业人士都处于那个维度,即说话的维度。
在担任少年法官的实践中,我经历过这样的事实:孩子与教育工作者,甚至可能是父母一起参加教育援助听证会。对我来说,非常重要的是——正是这种实践让我走到了这一步——能够让自己脱离观众,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: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互动、教育者的位置等等。对我来说,孩子和他父母的手势都表明了一些重要的事情。
在法律上孩子的话是否具有特殊地位?
在获得特殊地位之前,儿童的言语是治安官管辖的事项。他们关注未成年人的听证请求;这是一个令他们担心的话题。一些家庭法庭的法官希望授权:他们有时认为儿童保护工作人员由于接受过培训,更有资格进行这些听证会。
在教育援助听证会上,我听取了数百名 智利电话号码库 未成年人的发言。这是完全不同的,因为我们与教育工作者、社会工作者、心理学家,有时还与儿童精神病学家合作。就我个人而言,单独听未成年人说话很容易,但需要澄清的是:我不确定未成年人是否在告诉我事情。
每一个主体都是先被他者的言语诉说,然后 SEO 审核可以被描述为识别可能 才能够依靠言语本身。如何评判一个陷入如此困境的主体?
在其法规中,法官肩负着保障个人自由的使命。当儿童成为法律裁决的对象时,会有第三方来制止法官可能超越其必须具有的中立性。
孩子是我们倾听的人,但与此同时,我们必须对他作为人的身份保持距离,以便恰恰保证他的自由。孩子说的话我们会认真听取,并采取安全措施。例如,孩子们可以从律师、临时管理员那里受益——这是很基本的。律师是保障者,他受过这方面的训练:他是律师协会的一个专业团体的成员,他以前见过这个孩子,并且和他进行过面谈。与去办公室会见的法官相比,孩子与自己的律师交谈当然拥有更大的自由,因为法官的谈话会显得更加严肃。
真相可能原来是“谎言”
孩子们有时会利用这一点。您在实践中是如何考虑到这一点的?
过去二十年里,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: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。被告和被指控的人可以撒谎,律师可以为撒谎的人说话。三十年前,被告必须说实话,而且他所说的真相必须符合案件档案和法官的个人信念。如今,真相已从客观的科学证据中浮现出来。在刑事案件中,已经不存在任何供述,所以这个词不被考虑。任何不愿意认罪 柬埔寨号码 的人都有撒谎的权利,即使他已经犯了罪,因为他的罪名将基于科学警察提供的证据。因此,随着事态的发展,我们必须保持客观:我们需要一些因素来证实这一说法。
从制度和历史角度看,言论的分量和权力已经相对化。我们说: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待事物的方式。
自奥特罗事件发生以来,法官对儿童说话一直十分谨慎。如果我们想验证孩子的话,我们需要儿童专业人士。在某种程度上,孩子的话语要经过筛选。它是時間的筛子。一个孩子将要从教育支持中受益,或者将被送入儿童之家,也许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,真相才会浮现出来。
当法官面对一份演说时,他总是要心存疑虑。他是个人自由的保障,并对这种言论提出质疑,无论是成年人的言论还是儿童的言论。
在一个文件中,我们可以有多个事实。法官做出的判决可能会侵犯个人自由。当你安置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法官必须在所有这些事实中找到一种方法来做出最佳判决。我们有责任和职业道德。